
来源:中国东坡文化网 发布时间 2025-06-10
《别后》
序
有一种相思叫《别后》
2017年7月,甘棠书院联合百可园诗社在上海举办诗人媒体见面会。之后,我和甘棠书院院长吴启民先生,召公文化研究会副主任、陕西诗人钱晓强先生,百可园诗社社长汤国华先生一起同去浙江平湖行知中学讲课,并举行诗歌改稿会。
会后,双鹏兄自台州赶过来与我们相聚。此后,我们一行四人从平湖李叔同纪念馆出发,到访了莫氏庄园,桐乡乌镇,然后自湖州去三门峡,过西安抵铜川,后到李世民的行宫玉华山,唐玄奘译经的玉华寺等地一路采风学习,由此拉开了我们交往的序幕。
斗转星移,季节无声交替。不知不觉中我们交往已九年之久,期间偶有联络,但终未能见面。近期听闻双鹏兄大作《别后》即将结集出版,倍感欣慰。读罢书稿后鼻尖不由得一阵酸楚,颇有感概,遂以寥寥数语,置于卷首,以期抛砖引玉,揭开《别后》全文神秘面纱,领略其文字惊艳之美。
如果你觉得你所在的城市依旧喧嚣,你的心境不复以往的纯净。那么请你读一读《别后》。这里娓娓诉说着一个中年男人最纯情的浪漫。全文通过对往事的回忆,通过时间、时空和地点的转换,通过穿插大量情感陈述和景色的渲染,让情感荷尔蒙层层发酵,通篇弥漫着对木碗的相思和对十年中已流逝时光的留恋。
“天空寂静,她会在我消失不见后,故作坚强的独自买票回去。我们坐上不同朝向的两辆班车,看着各自窗外的景色:起初都差不多,慢慢的庄稼和地形都会逐渐不一样,直到出现不同风格的建筑。”就这样离开,终不再来。让我想起了刀郎的《花妖》,终生都在寻觅,但时空错乱,不得相见。最后只愿把我的心像流沙一样放逐在车辙旁,甘愿做你年轮上流浪的眼泪。正如作者文中描述的:“我那会儿也并不知道,我将完全退出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不再可以陪伴或是安慰对方,只留给对方被风雪模糊的回忆,任由她在岁月中跌跌撞撞的自己成长。”
那是一段多么漫长的漂泊,你的,我的。像我儿时用玻璃瓶困住小鱼去观阅那样,我那时亦经历着涸辙之鲋:像车辙印里的小鱼,被生活用小洼困住,囊中捉襟见肘的羞涩,既无远见,也无前路......除了你的欢喜,再一无所有。
曾几何时,我们会在转身与回眸之间蓦然发现,你刻骨铭心思念的人,恰恰是你从未得到过的人。黄河奔腾不息,鄱阳湖水草茂密,我曾在婺源的徽派建筑群里看过今生最多的桥,也曾早你几年登临过黄鹤楼,看长江楚天横渡。
思念终是破冻,在心里发了芽,终在故乡潢川饱经情绪消 磨,失眠许久。少年归来不年少,以38岁的期待和妄想,去描述18岁的羞涩。在盐碱地中成长,在许多挫折和冷言冷语中去叙述一个十年前的纯情。我记得日记本里的夏天和那天夕阳,我与你在蔡明园的广场静待日落,蛙声一片时,我们只有手牵手的赤贫夜晚,聊着那些一文不值的平仄。
“还记不记得?你说,等冬天来了,就陪我一起看雪景?只能说,时间过得真快。我已走到了过去说好的未来。
未来已来,而故人不再,生活中我们有多少这种月有阴晴圆缺的挣扎和无奈?那个少年懦弱且腼腆,读过几本屈指可数的书,就以为可以遮挡丑陋。这多么像极了昨天和今天的你我。在生活的天平上,他始终不愿意放弃质证,始终走不出对青春的庭审,难以与少年的自己签订一份调解协议。
完成不了自我救赎,就用文字来自救。除了这样,我们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让今天的中年去接受和回忆曾经的少年吗?风卷起窗帘,阳光像个偷渡的小孩...就连阳光也偷偷摸摸的照进来不忍心打乱那曾经年少的心和心底的那一抹倔强的纯情。
如果上天能满足我一个心愿,我想这也会是作品中“我”的心愿。我期盼能通过《别后》的出版发行,或许在某一个晨曦微露的清晨,某一处秧苗青青的田野,或于朔风中洋洋洒洒的等待中,或于月上柳梢的暮晚里,我们能够在不经意的回首之余,发现木碗,找到木碗。
双鹏兄《别后》结集出版之际,谨以此文抛砖引玉,是为贺,是为序。
乙已盛夏东坡三十二世孙:琅琊居士苏循堂
读李双鹏先生《别后》偶感并序
【作者简介】
苏循堂(苏斌),汉族,诗人、作家、编辑。东坡三十二世孙。字文武,号一谡。山师大汉语言文学专业。1998年加入北方文研所,师从著名作家张贤亮。2000年自编散文集《无话可说》诗集《青春如歌》。2018年受聘为《315记者摄影家》鲁南融媒体中心主任;北京正念正心国学文化研究院常务工作委员会委员,院士、客座教授。2023年受聘为CCTV《商企汇》、CCTV《诗画中国》栏目组编导;2025年受聘为《新时代法制新闻网》普法中心副主任;同年5月筹建《中国东坡文化网》,兼任总编辑。中华诗词学会、中国诗赋学会、中国网络作家协会会员,北研所作家创作中心研究员,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召公文化研究会顾问,东坡诗社社长。代表作有《十连环》、《东坡园记》、《芦山堂赋》等。
一 、 木 碗
别后,是那个叫木碗的女孩,给我写过的一篇文章,题为《别后》。
“细细算来,我们分别已经很久了,那时你穿天蓝色的衬衫...... ”看久了,对别后这两个字就格外有感情。
而木碗原本的笔名是“暮晚 ”。我们曾在红太阳超市闲逛时,买了两只木碗,她起初并未察觉我为何要买碗,我说此与暮晚谐音,她恍然大悟,自此就将笔名从暮晚改为木碗了。


她那时写《别后》,皆因我们在不能自食其力的年月,经历过一些不得不背过身的离别。成熟后才慢慢明白,别后这两个字,远远超出了它的字面意思,不仅仅是离别之后那么简单。而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孩子,她的留恋,不舍,她的思念等诸多复杂情绪的交织。

2013年的腊月,临近春节,阔别半年,我由浙江归来,蔡明园十分热闹。摇旱船、抬花轿、舞狮子等各式各样的活动还停留在回忆中,来自十里八乡的民间文艺者们汇聚在这座广场,演绎着各类节目,我们恰逢此处,是众多观众里的一对。
小商小贩们会带来各式的商品与小吃,套圈儿、打气球,骑 马和各类摊位,与广场上的人山人海一起组成暖人的回忆。

那会儿的蔡明园,广场还没有那些立柱。蔡明园的牌楼,也没有那么高的护栏,随手即可触摸那座宏伟、饱经风雨的建筑。
我与木碗漫步在这人山人海,在临近春节的喧哗中,在普天同庆的欢乐中紧握着属于彼此的幸福。

我们牵着手,漫步在明乘法师“ 回头是岸 ”的题字下。可惜日记本里并未记载那天都谈论过什么,去过哪些地方,我那会儿无比珍惜与她在一起的每一分一秒,无暇去细写日记,幸福也确实容易让人疏于笔墨,只记得那会儿的温暖与幸福。
那一次的离别,不像夏天,她最多只会送我到县里白云观大道旁的汽车站,或是再远一些的汝南汽车站,或者更远一些的平舆汽车站,直到这里,再往后已没有就近的停靠点,送君千里,才算一别。
陪同送别的来回车费已是她两三天的伙食费,我们趁着两辆车发车的间隙,坐在那个简陋的小站里,坐在那张刷着绿色油漆的木制靠椅。

随着发动机的嘈杂声淡去,扬起的灰尘也会慢慢落寞,直到像没有班车离去。
天空寂静,她会在我消失不见后,故作坚强的独自买票回去。我们坐上不同朝向的两辆班车,看着各自窗外的景色:起初都差不多,慢慢的庄稼和地形都会逐渐不一样,直到出现不同风格的建筑。
但心中满满都是对方。

我们那时相距只有短短的200公里,可在没有普及导航和交通工具的年代,两百公里已是天涯海角那么远,已是靠徒步和问路,从白走到黑都难以企及的距离,一别就不知何日再次相见,除了牵挂别无他法。
那个听着发动机轰鸣和窗外蝉鸣的少年,再不能用一张50元纸币就能买到的汽车票,换得满心欢喜,就能看到心爱之人好多好多眼,就能到达漂泊的岸边。
他的翻盖手机早已不知遗失在何处,新款的手机再也不会因为电量关机,或是因为没钱充值而欠费,却怎么也收不到对方的消息。
同是那年冬天,后来我与弟弟、妹妹又去了一趟,我们与木碗一道,从上蔡游玩至驻马店结束。那会儿县域的交通情况很一般,路况也差,我跟弟弟感慨,我们以后要是有一辆吉普车就好了。

她许是因为预感,许是因为不舍,虽小我近两岁,却比我思绪成熟,她送我到了潢川县,次日独自买票回去了。
我害怕父亲知晓而斥责,并未前去送她,那是2014年的1月14号,在日记本里,下了一层薄薄的雪,很快就停,我知晓她的情绪,那时我们还心连着心如同比翼,但我并未写上去,我以为有些东西不写就会忘记。
我那时并不知道,前一天的匆忙道别,是与你在距此的十年,甚至是今生里的最后一面。偏偏那次我们都以为很快就会再见,并未好好别过。
我那会儿也并不知道,我将完全退出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不再可以陪伴或是安慰对方,只留给对方被风雪模糊的回忆,任由她在岁月中跌跌撞撞的自己成长。
十年后的冬夜,我将车停在潢川汽车站门口,看见深夜出站的旅客,都被私家车或是出租车依次接走。听着邵帅的歌,我发了一条朋友圈记录此刻,说:十年前应该去送送你。
那是一段多么漫长的漂泊,你的,我的。

弟弟工作忙,不爱互动,评论说:“是驻马店的侉子吗? ”
是侉子呀,很多年都没见过了,我这个蛮子并未没回他。信阳与驻马店的方言略有偏差,他们戏称我们俩为蛮子与侉子。
冬夜里的伤悲并不会出现奇迹,你也不可能知道有人在这座小站将你等候。夜里回的都是长途旅客,且我知潢川到上蔡的班车早已停线。那是白天,售票员用异样的眼神告知我的,因为近乎无人询问这个地名,才导致停了这辆班车的线路,老员工的她有些惊讶。
那个女孩常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我那时并不知晓这个典故,多次询问,她都避而不说。后来明白,18岁的女孩子也是言行不一的,她长发披肩,举止与口中说的完全相反,她恰恰是相忘于江湖,不如相濡以沫。
像我儿时用玻璃瓶困住小鱼去观阅那样,我那时亦经历着涸辙之鲋:像车辙印里的小鱼,被生活用小洼困住,囊中捉襟见肘 的羞涩,既无远见,也无前路,除了你的欢喜再一无所有。(编辑: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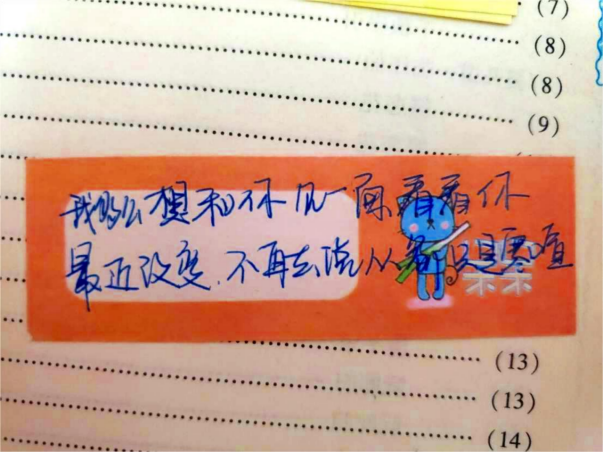
【编辑:苏循堂】





东坡风公众号

品读苏文化公众号

世界苏姓文化荟萃公众号